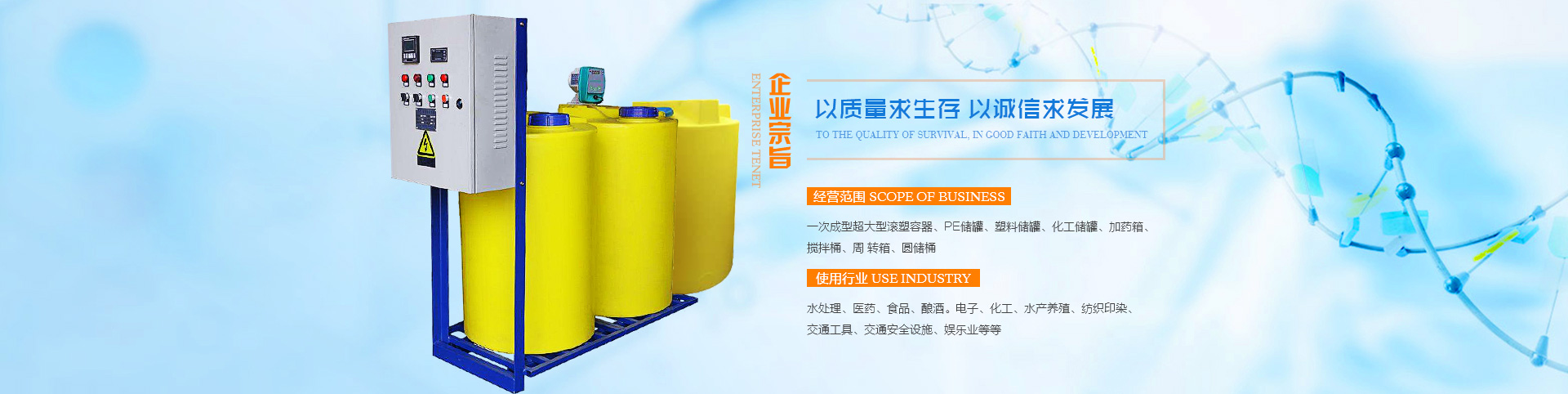




开云电竞:
这不是一篇传统的“英豪叙事”。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,动态新闻想把镜头拉回污浊的洪水里,让你看见最实在的“我国脊柱”:
文中的卫生员梁腊强、指导员李隽喆、班长周胜开……和一切的我国武士相同,是你喊一声“”,会马上转过头来回应的人。在汹涌的激流里,他们的身影和很多官兵的身影堆叠、偎依,像一块块厚实的石头,垒成了老百姓心里最稳妥的岸。
看完这些,你或许记不住他们的脸,但一定能记住:当灾祸来袭,最早抵达的那些人,一定是——“人民子弟兵”。
榜首次是2025年6月24日清晨,像天上的水缸被打碎,暴雨将河水瞬间拉满,街灯影子撕裂成晃动的乱影。第2次是在五天后28日的黄昏,上游洪峰再次裹挟着树枝、家具,闷声撞进低洼的老巷。警报响起,商铺卷帘门没有落下,水已漫过脚踝;孩子们刚放学,书包还没放下,就被大人扛上了房顶。
就在这两场洪水的缝隙里,一抹抹“橄榄绿”融进了榕江的日与夜。武警贵州总队的千余名官兵快速集结,带着救生衣、冲击舟,还有轰鸣的挖掘机、推土机,在浓稠夜色里驶向最风险的低洼地带……
漆黑像一锅稠墨,卫生员梁腊强把肩上的药箱往上一提,塑料箱角撞在铁扶手上,“咚”一声闷响。他下意识用手护住箱盖——碘伏、纱带、抗过敏药,排得比枪膛里的子弹还密。
新一轮洪峰扑来,榕江县城水榭榕城小区再次被淹。退伍老兵王涛一直在抗洪清淤一线,回身却被洪水挡在家门外;电话那头,妻子潘胜花强撑着平稳的声线,却掩不住孩子的哭闹声和窗外的雨水声。
6月29日上午10点,一道穿透阴霾的男声在她简直握碎的手机里响起——这是武警贵州总队救援官兵的来电。
两小时前,暂时驻点的铁皮房顶被雨打得噼啪作响,灯泡晃得人影乱动。梁腊强正在为一名兵士缠最终半圈胶布。
胶布“刺啦”一声剪断,他顺手把两片葡萄糖塞进对方口袋,“含一片,省得没力气。”
此刻,梁腊强的对讲机遽然响了起来:“6栋11楼,60多岁白叟加俩娃,当即声援!”
半瓶矿泉水被他往桌上一放,瓶里水旋出一个急迫的漩涡——漩涡还没停,人现已冲进雨幕。
“卫生员,我全身痒得钻心!”此刻,兵士魏信猛地留步,迷彩袖口鼓出一串红疙瘩,雨水泡出的湿疹正疯长。
再往上,楼梯陡成山崖。官兵们敏捷分工:有人搀扶腿脚不方便的王涛的父亲,有人当心抱起孩子,有人替潘胜花扛起了家里需求搬运的物资。
下楼比上楼更难,每一步都踩进不知道的黑洞。梁腊强把药箱挪到前胸,武装带勒进锁骨,三岁半的娃娃趴在他背上,小手攥着他领口榜首粒纽扣。

几天后,洪水退去,常驰广场负一层的合力超市像一头巨兽打开的大嘴,半尺厚的淤泥散着腥臊。兵士们排成人链,把泡胀的米袋、变形的纸箱往别传。
兵士余海鑫在最里侧,预备把其他兵士装好的淤泥扛出去,遽然“砰”一声——一只木箱被水泡散炸开,一团黑泥击中他右眼。
安全绳扣在余海鑫腕上,另一头缠在梁腊强掌心,把脉息调成同一频率。淤泥没过脚踝,每拔一步都像拔萝卜。余海鑫闭着眼,只凭手腕上那根绳的牵引,跌跌撞撞往外挪。
到门口,梁腊强把他按在台阶上,用生理盐水冲眼,冲出的黑泥水顺着下巴流到胸口。
梁腊强蹲在空位清点药品,黑色签字笔在清单上划出一道道粗杠,像在地图上符号一条条刚打通的街巷。
月亮从云缝里漏下一缕银光,照亮他的影子——背药箱的姿态,像一棵负重的树,枝条却尽力向天空扩展。
洪水退后,菜叶、鸡毛、死鱼、沙发凝成黑褐的“沥青”,30厘米淤泥混着碎石,一脚踏下,“噗嗤”咬住小腿。
他榜首个陷进去,拔腿时回头低喝:“踩我足迹,别踩空!”声响决断有力,把困难前行的部队钉成一条线。
遽然,淤泥深处宣布“咔”的脆响。他拨开浮着的烂菜叶,显露块泡得发胀的门板,沉得像灌了铅,半截锈铁锁还死死挂在上面。李隽喆单膝跪进泥里,膀子顶住门板下沿,喉结翻滚着喊:“朱钰坤,搭把手!”
“来了!”列兵的声响裹着热气撞过来。朱钰坤扑过来托住门板另一侧,两人臂膀上的青筋一同暴起。
黄昏6点,落日把整条巷子染成了锈赤色。小推车的轱辘声歇了,只剩此伏彼起的粗喘。
李隽喆愣了半拍,咳出一口喉咙眼的咸腥,喉结一动,哑着喉咙起了调:“山知道我——江河知道我!”
起先三两个人跟着哼,后来整条巷子都响了起来。铁锹当麦克风,甩出的泥点划成闪亮勋章;跑调的、破音的、呜咽的,一切声响都被热浪卷在一同。
声响撞在断壁破瓦上,弹回来时带着颤,周边有大众悄然抹眼。歌声一落,李隽喆又变回了那个抠细节的指挥员:“朱钰坤,门板再撬十公分!陈小红,钉子拔完别跳,单脚蹦简单崴!”沙哑里藏着不容置疑的笃定。

李隽喆抬眼,灯在眼底映出两粒亮团:“等路通了,等早点摊支起来,你的榜首根油条算我的。”
远处,几个兵士靠在墙边上睡着了,鼾声混着虫鸣在夜里荡开。李隽喆放轻脚步走过去,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盖在列兵何江身上,像给一株小苗挡风——这孩子下午差点中暑,脸白得像纸。
清晨5点,最终一桶淤泥被抬上货车。李隽喆叉着腰站在街心,浑身的泥浆结了层硬壳,像穿了件不合身的盔甲。他和战友心里都装着同一句话:快点把路清出来,让阿婆的早点摊支起来,让孩子们能踩着洁净的路回家。
天亮了,一位扎围裙的阿姨抱来西瓜,切好放在家门口:“孩子们,吃一口甜的!”
李隽喆折腰捧起一块,咬下一口,甜得眯起眼:“阿姨,您这瓜比嘉奖令还管用。”汁水顺着指缝往下滴,混着泥,竟成了最洁净的色彩。
李隽喆没说话,悄然把钱塞进阿姨围裙口袋。“您不收,这瓜咱们可不吃。”他掌心的泥印蹭在阿姨的围裙上,像朵深色的花。
栏杆外,住校生挤成一排。高个女孩踮脚举纸板——雨水泡皱的壳子上,红笔歪歪扭扭写着:“叔叔,你们最帅!”
班长周胜开每挥一次铁锹,都像把一块吸饱水的海绵生生扯出泥潭。汗珠顺着发梢滚落,在下巴尖颤了颤,砸进泥浆里,连“嗒”的一声都来不及响就被吞没。
他应了一声,把铁锹当拐杖,一步一步往外挪。戒备线外,排长举着手机,屏幕亮得扎眼,像黑夜里仅有的手电筒。
周胜开接过电话,听筒贴耳的瞬间,听见自己呼哧呼哧的喘气,像破风箱撞着麦克风。对面传来妻子衰弱却清亮的声响,布景里掺着婴儿细碎的啼哭。
“周先生,听见没?”妻子在笑,嗓音带着产后的沙哑,“小家伙7月1日清晨五点整出来的,七斤,嗓门可亮了。”
三天前紧急集合时,视频里妻子还摸着圆滚滚的肚子,冲他摆手:“别急,预产期还有六天呢。”他其时拍着胸口确保:“等我回去。”成果一脚迈进洪水,手机就被锁进营区柜子。200多条信息像无声的焰火,在漆黑里炸开又平息。
“怎样不说话?”妻子带着点狡黠,“是不是吓着了?我就知道你没预备好。”
“姓名……”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,“周以墨。相濡以沫的沫,改个谐音——墨。你说的,男孩子得沾点墨香,也得有节气。”
对面静了半秒,吸鼻子的声响透过电流传来:“周先生,你怎样遽然会说话了?”
他想笑,眼眶却先烫了。垂头看自己的手,指甲缝里嵌着黑泥,虎口血泡破了,干成褐赤色的痂。几天前他蹚水进来时,只来得及发一句“紧急任务”。他乃至不敢细想,妻子是怎样一个人躺在产床上,把疼熬成拂晓。
“不急,”妻子悄悄笑,“我和以墨等你。你把那儿的活儿干好,别让孩子笑话他爸。”
电话挂断,周胜开把手机还给排长,回身往淤泥里走。有战友凑过来玩笑:“胜开,当爹了还不请客?”他没回话,只折腰抄起铁锹,往更深处插去。铁锹好像轻了,掌心的疼也轻了。

夜里,暂时驻地的灯泡透着朦胧的光。周胜开捧着自己那部沾泥的手机,屏幕上的200多条未读信息像一串沉重的省略号,他一条一条往上翻:
第二天清晨,薄雾未散,榕江老街像被一层轻纱罩住。周胜开榜首个扛起铁锹冲进淤泥,雨鞋踏在烂泥里宣布“咕咚”一声闷响,像给整条街敲了起床鼓。
战友们看见,他干活时总不由得咧着嘴,雨鞋踏泥的节奏比平常快了半拍。正午,炊事班把盒饭送到戒备线外。周胜开蹲在路周围,饭盒里是青椒炒肉和紫菜蛋花汤。他扒了两口,遽然想起妻子产前最馋的,便是一家小店的青椒肉丝。老板总爱多放一勺蒜末,辣得她鼻尖冒汗。
“想啥呢?”近邻班的兵士周聪凑过来,一坐在他周围,“传闻你小子当爹了?”
“嗯。”周胜开把最终一口饭扒洁净,又跳进没过小腿的泥浆里。“得赶忙把这段沟清出来,回去抱抱儿子。”
周聪把铁锹往泥里一插,咧嘴坏笑:“姓名起了没?要不叫‘周清淤’,听着就接地气!”
清淤第七天,最终一车淤泥被运走。戒备线撤消时,居民们涌上街头,将煮熟的红鸡蛋和绣有“安全”二字的鞋垫,一股脑儿塞进官兵的怀里。
返程大巴发动前,排长递给周胜开一张盖有红章的纸:“批了休产假,回家抱儿子吧,晚上别打呼噜吓到以墨。”
他闭上眼,幻想妻子抱着孩子站在家门口,落日把两人的影子叠在一同,像一幅刚剪好的红纸窗花。而他,正从剪影外,大步跑进去——铁锹留在死后,像插在拂晓里的一面旗。

只因那天,从高处看,兵士们绷紧身体、奋力拉车的容貌,在脚底淤泥的衬托下,宛如一幅油画,催人泪下。
现在,清晨的阳光落在坡面,这条25米长的坡道已看不出往日的难堪。当地正式给它命名为“脊柱坡”——不是留念,而是把一段滚烫的前史,揉进日常的呼吸里。
现在,榕江的鼓声与欢呼声再度响彻“村超”球场,整座县城以最隆重的典礼,迎候曾拼命看护他们的亲人:来自全国各地的救援部队。
据守哨位的武警官兵不能到现场,但从新闻报道里读懂了这份滚烫的挂念。都柳江岸,灯光映笑脸,一曲军民鱼水情,唱得山河动容。